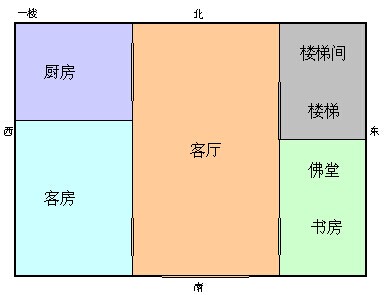儒家書籍能辟邪嗎 分析儒家和道家的異同
內容提要:儒家修身學最早見於《五經》,經歷了以培養“君子”為目標的“德性—德行培育”到以“成聖”為目標的“心靈操練”兩個不同的時代。而在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過渡時代”中,儒家修身傳統被轉化為培育“新君子”(國民、公民)與“新聖人”(“革命聖人”)的精神資源。當今,我們正在步入另一個“過渡時代”,一個“人禽之辨”的2.0版本(“人機之辨”)的時代,如何回應這個“加速化”與“全球化”成為不可逆轉的時代所提出的人類生存的根本問題,如何重新啟動儒家修身學資源,是當今建設哲學的“中國話語”必須重視的問題。

儒家擁有一個源遠流長的“修身”傳統。這個傳統宛若黃河長江,蜿蜒浩蕩,奔流不息,惟於高處俯瞰,把握其大轉折處,方能瞭解其大勢與脈絡。本文嘗試將儒家的修身傳統劃分為四個不同的時代:(1)隨著遊士階層的出現,而於春秋戰國之際形成了德性—德行培育的時代,修身的目標是“君子”,修身對治的焦點是德性—德行的培育。(2)隨著平民社會的到來,而於唐宋變革之際形成了心靈操練的時代,“工夫”(“功夫”)的目標是“成聖”,工夫對治的焦點是“意念”,工夫修煉範圍、深度均有重大拓展與深化(“夢”與“生死一念”成為工夫修煉的場域),靜坐、自我書寫等多元化、技術化的工夫技術日趨流行,“複其初”工夫論模式取代了先秦的“擴充”與“改造”模式。(3)隨著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蒞臨,而於清末民初之際形成了“過渡時代”,“覺悟”(“覺醒”)成為修身的關鍵字,修身的目標是培育“新君子”(國民、公民)與“新聖人”(“革命聖人”)。(4)當今,我們正在步入另一個“過渡時代”,一個“人禽之辨”的2.0版本(“人機之辨”)的時代,一個如何修身乃至修身是否必要皆成為問題的時代。
一 “修身”:德性—德行培育的時代
修身的觀念在《五經》中已經出現,如《書經·皋陶謨》《逸周書·周書序》已有“慎厥身修”“修身觀天”“修身敬戒”等說法。周公明確地將“天命”與“德”聯繫在一起,原本“嗜飲食”“不歆非類”的天、神轉而成為超越族類、超越世俗物質利益的“饗德”“惟德惟馨”“惟德是輔”的道德神。就此而言,西周政治文化已經具備了“崇德貴民”的人文主義底色。代表世俗的道德理性與政治理性的“地官傳統”逐漸壓倒了以神靈祭祀為核心的“天官傳統”,與此相伴,禮樂文化之中的儀式意義逐漸內化為德性,“儀式倫理”向“德行倫理”過渡是春秋時代的時代精神。①周人“敬德”觀念,誠如徐複觀指出的那樣,其背後的“憂患意識”具有“道德的性格”。然而,我們也不能忽視這一現象,即周公對德行的重視其根本的目的始終未脫離“獲得天命”“守住天命”這一終極視野。“敬德”與“受命”、“德”與政權的“天命”往往綁在一起。對“德”的追求雖不乏真誠與堅定(“厥德不回”),但其動機卻始終無法超越政權的“受命”這一向度(“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②
孔子堅持有教無類,使得修身帶有開放性,在原則上它不限定在某個階層上面,後來的《荀子·君道》與《禮記·大學》都明確指出,上自天子下至臣下、百吏乃至庶人皆以修己、修身為本。孔子(《論語·述而》)始又強調“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孟子·盡心下》則說:“哭死而哀,非為生者也。經德不回,非以幹祿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顯然孔子對德行的追求不僅具有了普遍性,而且也具有了純粹性。由“受命”向“俟命”、由古老的“善惡有報”宗教信念向德福剝離、由“行仁義”向“由仁義行”,德行自此獲得了自身的純粹性與自足性。餘英時指出,春秋的前半段,大約西元前七世紀中葉(孔子出生前一個世紀左右),“修德”已成為“精神內向運動”的主題:與王朝“天命”相聯系的集體和外在的“德”逐漸轉為個人化、內在化的“德”,但這個“德”僅限於諸侯、執政、卿大夫,而仍未及一般人;另外這個“德”雖已開始“內在化”,但以何種方式內在於人,亦指示未清,此中關鍵尚未出現“心”的觀念,故這個時期只能稱為軸心時代的“醞釀期”。③在此需要補充的是,在孔子之前,“德”尚未完全證得其自身的普遍性、純粹性與自足性。另外自孔子開始,人與禽獸之別的話語開始見於不同的文獻。先秦諸子不約而同地將“禽獸”視為映射人之為人的“他者之鏡”,人禽之別話語的出現標誌著人之“類意識”的自覺、“做人”意識的自覺。人之“天爵”“良貴”說將人之“貴”由世間差異性的社會地位提升至人人皆具的超越性身位,不僅構成了人皆可成聖的人性論的超越根據,也構成了傳統向現代不斷轉化的精神資源,譚嗣同“仁以通為第一義”“通之象為平等”這一近代“仁說”未嘗不可視為是對這一精神資源的重新啟動。
孔子不僅形成了有教無類的普遍人性意識,更明確提出了“修己以敬”的主張,這是一種整體生命的省思意識、一種反思性的處己態度、一種徹底的自我負責的態度(“為仁由己”,“我欲仁,斯仁至矣”)。毫無疑問,它反映了對自我德性生命的一種高度專注。“敬”之一字更刻畫出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對“自我”的一種特殊的關注方式,而與“修身西學”中的“關心自我”、福柯(Michel Foucault)所謂的“自我技術”形成了鮮明對照。另外,孔子還提出“躬自厚而薄責於人”這一反身修德的自反性的人生態度,奠定了儒家“君子必自反”的修身路徑。“君子”則是修身的目標。觀《論語》開篇《學而》“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到卒章《堯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君子始終是孔子認定的修身目標。據楊伯峻《論語譯注》統計,二十篇中記載孔子及其弟子論“君子”的有八十六章,出現率最高詞是“仁”(109次),其次就是“君子”(107次)。而修身對治的焦點一方面是“仁”之精神的植根與培養,另一方面則是言行舉止的修飾。《尚書·洪範》已有“敬用五事”的古訓,五事即貌、言、視、聽、思:貌恭、言從、視明、聽聰、思睿。《國語·周語》單襄公更是明確指出:“夫君子目以定體,足以從之。是以觀其容而知其心矣。目以處義,足以步目。……視遠日絕其義,足高日棄其德,言爽日反其信,聽淫日離其名。夫目以處義,足以踐德,口以庇信,耳以聽名者也,故不可不慎也。偏喪有咎,既喪則國從之。”君子之“視聽言動”關乎國之存亡,可不慎乎!孔子四勿之誡(非禮勿視聽言動)實淵源有自。《禮記·哀公問》載哀公問孔子何謂“敬身”,孔子答曰:“君子過言,則民作辭;過動,則民作則。君子言不過辭,動不過則,百姓不命而敬恭。如是,則能敬其身。”《周易·系辭上》雲:“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論語·泰伯》曾子將君子之道歸結為三:“動容貌”“正顏色”與“出辭氣”,而在子夏君子三變之說中(《論語·子張》),“望之儼然”即是“動容貌”,“即之也溫”即是“正顏色”,“聽其言也厲”即是“出辭氣”,由此亦不難窺見孔子君子人格教育之重點所在。《論語·述而》所記孔子教學的內容為“文、行、忠、信”:文,先王遺文;行,德行;忠,盡力做本分之事;信,誠信待人。此“四教”均不外乎君子德行之培育。而所謂的“四科”(德行、言語、政事、文學)以及“君子之道”(行己恭、事上敬、養民惠、使民義)亦均著眼於實際行政能力的培育。
實際上“士”之本義即“事”,觀《尚書》《詩經》《禮記》《荀子》等書籍中“多士”“庶士”“卿士”一類術語,“士”均與“事”聯繫在一起,士即是在政府部門中擔任某種“職事”的人。故“士”又通“仕”④,這從一個側面說明,士階層即是通過學習政治、軍事、禮儀的能力而獲得從政、出仕的群體。不過,春秋之前的士受到“三重身份”的限定,就社會身份言,士被限定在封建貴族層(當然是最低的一層),就政治身份言,士限定在各種具體的職位上面,而在思想層面言,士則限定在詩書禮樂等王官學的範圍。士的這三種限定也限制了它的“視野”,使得它不能真正超越自己的身份而形成對現實世界全盤的反思能力。⑤而“士”在春秋時代成為“遊士”之後,喪失了原來“有限”的身份,卻也因此形成了“無限的”視野,“處士橫議”,“不治而議論”“不任職而論國事”成了一時之“士風”。儒家的偉大在於,自孔子始,就給這個新出現的“士”階層注入了一種“道德理想主義的精神氣質”,對“士”階層提出了更高要求:“士”絕不能為“仕”而“仕”,“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仕”是有原則的。“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餘英時指出,先秦的修身觀念與士之出處辭受有不可分割的關係,中國士代表的“道”跟西方教士代表的“上帝”都是不可見的至高權威,惟上帝的權威則由一套教會制度得以體現,而“道”的權威自始就“懸在空中”,以道自任的士惟有守住自己的人格尊嚴、自尊、自重,才能顯示出其所抱之道的莊嚴性(“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才能與王侯之“勢”分庭抗禮⑥,這是先秦諸子重視治氣養心修身之道的原因所在。
孔子之後,孟子與荀子對儒家修身思想均有所推進。心—氣—形(身)的三聯結構則是兩人共同的修身路徑之預設:以“心”統攝“氣”,讓德性(“德氣”)滲透於人之身體並表現於言行舉止、動容語默之中(“見面盎背”“踐形”“美身”“有諸內,必形諸外”“著乎心,布乎四體,形乎動靜”“誠於內而形於外”)。⑦固然孟、荀修身的具體方法有異,孟子採取的是一種由內而外的“擴充”模式(development model),荀子採取的則是一種由外而內的“改造”模式(re-forming model)⑧,二人對“大丈夫”“士君子”的人格亦各有精彩之描述,但究其實質都未超出“君子”這一目標,要之,通過心—氣—形的聯動而像蟲蛹蛻變一般(“君子之學如蛻”)形成新的自我(“君子”),這是先秦儒學修身傳統的共法。
二 “工夫”:心靈操練的時代
“功夫”“工夫”,原義為“役夫”“役徒”及其所擔負的徭役工作,由此而衍生出“做事所花費的時間、精力”,而由花費時間、精力做某事而成就某種能力、本領、達到某種造詣,亦成為功夫、工夫進一步衍生義。最初佛教將造塔一類工程所需要的人力、物力稱為“功夫”,後又將佈施一類活動稱為功夫,功夫即“功德”,再後,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均被稱為功夫。其中“禪定”與“智慧”二門視為成佛的關鍵,故在唐代開始的佛教典籍中,功夫通常就是用來指坐禪這種修養方式,而坐禪既要求身心的高度專一,又有一套儀式化的操作步驟、每一步驟都包含了許多具體的要求,於是,在佛教那裏,工夫、功夫義最終變成了“個體將其身心進行高度的集中,以投入某種具有可重複性、竅門性、進階性的儀式化操作技法”。⑨
佛教的興盛,讓有精神追求的士大夫趨之若鶩,“儒門淡泊,收拾不住,皆歸釋氏”。儒學的復興靠“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的“野蠻”政治舉措,只會落入“攻之暫破而愈堅,撲之未滅而愈熾,遂至於無可奈何”這一尷尬境地,惟有“入室操戈”、“修其本以勝之”,方是正途。於是闡天道之密義、剖性命之微言、揭成聖之工夫便成了新時期儒學理論建構的主題。機緣到了,《中庸》(天道性命之書)與《大學》(內聖外王工夫指點之書)遂從《禮記》之中脫穎而出成為獨立的經典,而與《論語》《孟子》構成儒家的新聖經系統。⑩而就“成聖”功夫指點而論,堪與佛教具有重複性、竅門性、進階性的儀式化操作方法的“工夫”論媲美的惟有《大學》之“三綱八目”說。宋明儒不約而同地從《大學》之中擇取二、三字作為為學“宗旨”(11),良有以也。
而於《大學》所指點“工夫”中,“慎獨”成為“理學”與“心學”共同聚焦的“一環”。與漢唐儒將“獨”理解為“閒居之所為”不同,朱子創造性地將“獨”理解為私己的、隱秘的心理空間概念,對這個私己的、隱秘的心理活動之“知”並不限於獨自一人之“閒居”,即便是大庭廣眾之下、在與他人共處之際,仍是獨知之範疇。而對“一念萌動”之覺察、審查變成為慎獨、誠意工夫的關鍵,這是決定人之命運的“一關”,過此“一關”,方是“人”,否則即是“鬼”。作為工夫範疇“獨知”的提出,誠是儒家慎獨傳統中的“朱子時刻”。儒家工夫遂發生重大的轉折,其表現有如下七端:
第一,意念的對治成為工夫修煉聚焦之場域。早在北宋,“意念管理”即成為士大夫修身的一項重要內容。司馬光嘗患思慮紛亂,有時竟中夜而作,達旦不寐,後來則“以中為念”鎖定心猿意馬,即是著名的例子。趙概為澄治念慮,於坐處置兩器。每起一善念,則投白豆一粒於器中。每起一惡念,則投黑豆一粒於器中。至夜,則倒虛器中之豆。觀其黑白,以驗善惡之多少。初間黑多而白少,久之,漸一般。又久之,則白多而黑少。又久,則黑豆也無了。這種以數黑白豆或紅黑點多寡為修身工程的例子充分體現出宋明理學工夫“內轉”的特點。意念的對治在儒家修身傳統中催生了新的省思方式、省察類型。在先秦修身傳統中,夫子開啟了將人生整體作為一種對象加以反思模式:“志於學”(十五)、“而立”(三十)、“不惑”(四十)、“知天命”(五十)、“耳順”(六十)、“隨心所欲不逾矩”(七十)成為人生德性生命不斷躍進的“路標”,讓每個人在其修身歷程中不斷校準自己的目標,而不至迷失方向。曾子“日旦就業,夕而自省思”“吾日三省吾身”則將每天的行為納為反省的對象。宋明儒更將每個當下的“意念”納為反省的對象,“念慮之正不正,在頃刻之間。念慮之不正者,頃刻而知之,即可以正。念慮之正者,頃刻而失之,即是不正”,這是在意念發生之後的省思;“思之是非邪正,良知無有不自知者”,此是在意念發生之當下的、同步的省察,此省察與意念為“並起”,“無等待,無先後”,完全符合現象學意義上的自身意識的界定標準。
第二,工夫修煉的廣度、深度均有重大拓展與深化。工夫不僅對治人之意識領域,更是深入到無意識、潛意識領域,“夢”成為工夫的場域。“對廣眾易,對妻子難;對妻子猶易,對夢寐更難”,借夢蔔學(“人於夢寐之間,亦可以蔔自己所學之淺深。如夢寐顛倒,便是心志不定,操存不固。”)、“夢後自責”“夢中用功”乃至“夢中悟道”等等現象的出現,表明儒家內省工夫之範圍涵括了吾人全幅的心靈生活。這不僅意味著反思的廣度之擴展,而且同時也表明省察的深度之加深,省思的目光已經深入到人性之幽深晦暗之領域。毫無疑問,這是心靈澄明工夫貫徹到底之體現。
第三,與個體的內省、省察的深化相伴而來的是修行共同體中省過生活。省察之光亦往往存在“燈下黑”現象,見人過易,見己過難,聖賢固會“聞過則喜”,常人卻難免文過飾非。陸象山指出:“人之精爽,負於血氣,其發露於五官者安得皆正?不得明師良友剖剝,如何得去其浮偽,而歸於真實?又如何得能自省、自覺、自剝落?”(12)就此而言,個體性的拯救(“究極自己性命”)離不開修行共同體的集體拯救(“共了性命”)。勸善、省過、疑義相質、師友夾持都需要一種“組織生活”,書院、精舍、盟會之出現均可說是這種共同修身需要的制度化、儀式化之表現。
第四,“生死一念”成為工夫修煉的對象。“未知生焉知死”,先秦修身傳統少討論死亡現象。佛教之所以能在中國廣為流行,依二程的看法即是因其以“生死恐動人”,此後人“皆以死為一大事”。劉元城對二程的說法頗不以為然:“世間事有大於生死者乎?而此事獨一味理會生死,有個見處,則於貴賤禍福輕矣。且正如人擔得百斤,則於五六十斤極輕。此事老先生極通曉,但口不言耳。蓋此事極系利害,若常論則人以謂平生只由佛法,所謂五經者,不能使人曉生死說矣。故為儒者不可只談佛法,蓋為孔子地也。”(13)王陽明再傳弟子王塘南更明確指出“世儒之必趨釋氏者,無他,彼以為釋氏能超生死而孔子不能也”(14)。而佛教高僧安然坐化乃至豫知死期等等現象更是給理學家留下了深刻印象,故在理學家的傳記、年譜死生之際的記載中,辭氣不亂、安靜而逝成為通例。至陽明心學一系“化生死一念”“尋個不歎氣的事做”(“真正仲尼,臨終不免歎口氣”)成為工夫修煉的一個重要議題,心學一系“坐亡立脫”“豫知死期”乃至推遲死期的現象亦屢見不鮮。死亡遂成為一種清醒意識,一種自主的事件。(15)
第五,工夫修煉日趨技術化、儀式化、課程化。自宋始,“靜坐”既是士大夫的一種生活格調,更是理學家日常工夫修煉的專門技術。收斂身心、見性悟道、養出端倪、觀未發氣象、觀生物氣象、省過訟過,靜坐在修煉工夫中發揮了重大作用。另外,書信的往來、問學遊記、日記、日譜、自畫像等等福柯所稱的“自我書寫”(self-writing)也是理學修煉工夫的重要技術。(16)
第六,工夫修煉的目標明確為“成聖”。“欲出第一等言,須有第一等意;欲為第一等人,須作第一等事”,成為理學家共同的人生期許。聖人的心性圖像充分汲取了佛道兩家的“明鏡”意象(“聖人用心若鏡”、“大圓鏡智”),《論語》中“空”“無”“空空”術語被詮釋為聖人心體當空屬性。物來順應、應而中節、過後不留、“心中不可有一物”,聖人心性中之“無”的一面得到了空前的彰顯。唐宋變革,中國步入“平民社會”,人皆可成聖、滿街皆聖人的信念更是不脛而走。
第七,“複其初”模式(recovering model)是宋明理學的普遍的工夫論模式。(17)這一模式設定“本體”(“明德”“天德”“良知”“本心”)原是自家“天然完全自足之物”,故工夫只是“使複如舊”。朱子說“今之為學,須是求複其初,求全天之所以與我者始得”,他更是將孟子的“擴充”話語巧妙地解釋為“充滿其本然之量”的複初工夫。王陽明說:“吾輩用功只求日減,不求日增。減得一分人欲,便是複得一分天理。何等輕快灑脫!何等簡易!”王龍溪則說良知不學不慮,“終日學只是複他不學之體;終日慮,只是複他不慮之體”。無疑,陽明說“良知愈思愈精明”,就此而言,良知亦有一“成長”“充拓”“發展”的過程,但這只是就“良知”當下呈現、實現的“實際狀態”而言的,究其實這一“發展”話語最終還是要回復到那原初的完善的本體。
三 “覺悟”:“過渡時代”修身的關鍵字
清末民初是中國“天崩地裂”的“過渡時代”。用列文森(Joseph R.Levenson)的話概括,這個過渡時代就是一個使“天下”成為“國家”的過程。(18)由傳統“天下”視界下的“中國”向現代“世界”視界下的“民族國家”的中國之轉換、由“道出於一”向“道出於二”再向另類的“道出於一”(實則“道出於西”——先是“歐美之西”,繼而是“蘇俄之西”)的過渡(19),由傳統的天人合一、天—地—人存有的連續之道向“物競天擇”“與天爭勝”的“新天道”的過渡,牽涉到“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其中充滿著滿漢、古今、中西、新舊之糾結與緊張。這個大變局涉及政治制度、經濟與社會生活、文化理念與價值觀念各個方面的轉變,這是一次全盤性的、結構性的轉變。這個空前未有的轉變反映在思想層面,便是各種一攬子解決方案的提出、各種“主義話語”的競相登場。這一變局在本質上可概之為“中國現代性問題”。
在這個過渡時代中,西方世界中的近代“民族國家”(nation-state)一如巴黎的“標準米”成為“國”之為“國”的標杆,中國“無國說”流行一時。宣導“鼓民力、開民智、新民德”的嚴複認定“最病者,則通國之民不知公德為底物,愛國為何語”(20)。“立於世界民族之林”或者說使中國成為“世界的中國”便成了中國近代思想的一個重要主題。梁啟超《新民說》明確提出:“凡一國能立於世界,必有其國民獨具之特質。”建設何種國家(“國性”)、培育何種“國民”(“民德”)自是一體兩面之問題。“固其群”“善其群”“進其群”的“利群之道”(有益於群者為善,無益於群者為惡)取代了基於血緣倫理的“孝道”而成為“放諸四海而准,俟諸百世而不惑”真理。成全自我的“為己之學”被代之以“成全國家”,為“成聖”而讀書被代之以“為中華之崛起而讀書”,“國家”成為最大的思考單位:“國也者,私愛之本位,而博愛之極點,不及焉者野蠻也,過焉者亦野蠻也。”“不及焉者野蠻”,甚好理解,“過焉者亦野蠻”則如何講?梁啟超解釋說,世界主義、博愛主義、大同主義此類事情“或待至萬數千年後”猶不敢知,而競爭為文明之母,國家則是競爭的最大單位(“最高潮”),國家之界限被突破,則競爭消泯,“競爭絕”,“毋乃文明亦與之絕乎!”文明絕,則重陷入“部民”之競爭,“率天下之人複歸於野蠻”。傳統的“獨善其身”被視為“私德”,而以此自足放棄對國家之責任則“無論其私德上為善人為惡人,而皆為群與國之蟊賊”,“謂其對於本群而犯大逆不道之罪,亦不為過”。宋明理學“民胞物與”“萬物一體之仁”之精神旨趣在於突破人己、物我界限(“無有乎人己之分,物我之間”),在梁啟超看來此天下同風的意識造成中國人“知有天下而不知有國家”,進而“視國家為渺小之一物,而不屑厝意”,更為重要的是,國家作為“大群”其成立“必以對待”,即“群”之為“群”必有一“界限”意識:對外競爭,故須善認“群外之公敵”;對內團結,故必不認“群內之私敵”。這種民族國家建構之中分清敵友的意識後來則成為中國革命的“首要問題”——只是在後者那裏,敵友的劃分是依照階級而不再依照國族,或者說階級敵人已經被放逐於“群”之外,不屬於革命“群眾”的隊伍。而根據現代某些政治哲學家的看法,劃分道德領域的標準是善與惡,審美領域是美與醜,經濟領域則是利與害,政治領域則是敵與友,把敵人明晰無誤地確定為敵人是政治誕生的時刻:“所有政治活動和政治動機所能歸結成的具體政治性劃分便是朋友與敵人”(21)。“仁政”與“德治”是傳統儒家政治哲學的基本精神,這種精神在根本上是一種消解現代政治的意識。在饑鷹餓虎、萬國競爭的叢林時代,民族國家體系的世界視界取代這種天下一家、天下同風的視界自是“大勢”所趨、在所難免。用康有為的話說傳統儒家的“天下義”“宗族義”必須轉換為純粹的“國民義”。
需要指出的是,傳統的“天下一家”觀念也一直沒有完全退出國族建構者的“世界”視界,康有為的“大同”論、譚嗣同的“有天下而無國”的“地球之治”論,這種“反現代性的現代性理論”(“反西化的西方主義”)一直綿延不絕。孫中山雖然一方面抱怨傳統中國之所以“不國”就是因為傳統的世界主義(實則是“天下主義”)抑制了“民族主義”,故當今中國應該大力提倡民族主義,不過他話鋒一轉,中國的民族主義包含著真正的世界主義精神,因為歐洲的世界主義是有強權無公理的世界主義,中國的世界主義是天下為公、大同之治的和平主義。即便是後來的社會主義、國際主義論述中,“天下一家”的雪泥鴻爪仍然依稀可辨。郭沫若在二十年代就稱:“馬克思與列寧的人格之高潔不輸於孔子與王陽明,俄羅斯革命後的施政是孔子所謂的‘王道’。”無疑,近代的世界主義論述究竟在多大程度是由傳統天下的觀念生髮出來的,而不是由“另類的西方世界”觀(一種紮根於基督宗教的烏托邦主義終末論的世界觀)投射給傳統而製造出來的,甚或是某種出於對“西方”愛恨交織的“兩難心理”激發出來的,仍還是值得深究的問題。不過20世紀的天下主義、世界主義、國際主義、社會主義跟以往的“天下一家”的觀念有著根本的區別,它不再是基於“親親”這一親情、血緣“家倫理”所推擴而成的“共同體”,而是由志同道合的“同志”所建構的高度同質化“社會”。(22)
這就意味著,無論是民族國家的建構、抑或是革命意識形態的營造,都需要一番傷筋動骨的“脫人倫”“脫身份”的改造活動。“國民”意識與“黨性”意識的“覺悟”“覺醒”便成了過渡時代修身的主題。梁啟超在1915年創辦《大中華》雜誌,發刊詞即以喚起國民的“自覺心”為宗旨。的確,惟有將人從各種宗教的、宗族的等等有機共同體之中抽離出來,將傳統的紮根於鄉土社會之中的“植物性國民”(丸山真男語)“連根拔起”,將之轉化為愛國、愛黨的一個“分子”(“國民之一分子”、“人道之一阿屯”),才能形成統一的國家意志、政黨意志以及全民、全黨總動員的能力。這也可以理解何以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軍國主義思潮盛行中國,“惟軍國主義是務,而宗法社會棄之如脫屣耳”。(23)於是,傳統的“身家”成了現代“國家”的累贅,套用章太炎的術語說,從家族倫常之中掙脫出來成為“大獨”,才能成就國家這個“大群”。傳統的“身—家—國—天下”的存有鏈條斷裂為“個體”(“身”、“大獨”)與“國家”(“大群”)兩截。“家”逐漸被視為“罪惡的淵藪”(24),作為“身家”的存在甚至也遭受到第一代新儒家的懷疑,稱“家庭為萬惡之源,衰微之本”的熊十力自不必說,即便是最為保守的馬一浮也感慨說,儒家即便程朱諸公亦未嘗不婚,儒者自大賢以下鮮不為室家所累。(25)“離家出走”方能真正成為無牽無掛、放開手腳做大事、創大業的“個體”。現代性中的個體其本質即是一“無負擔的自我”(the unencumbered self),即是“出離自身”的,即是“無家可歸”的。“這種不具有任何必然的社會內容和必然的社會身份的、民主化了的自我,可以是任何東西,可以扮演任何角色、採納任何觀點,因為它本身什麼也不是,什麼目的也沒有。”(26)於是原來旨在覺悟成聖的“身”被塑造為一種具有衝破羅網、敢於行動的革命覺悟的主體,原來的“為己之學”變成了帶有革命氣質的主體性哲學。傳統紮根於人倫共同體之中的“修身”變成了政黨信仰共同體之中的“修養”與超越人倫的“革命覺悟”“最後覺悟之最後覺悟”。
傳統儒家的修身思想、工夫修煉的技藝從人倫教化(“孝弟慈”)、為己之學、天下一家、萬物一體的儒家信念框架中“脫嵌”,並被“嵌入”現代民族國家與政黨政治的視界之中。這體現在“個人意識”與“團體意識”兩個方面。第一,就個體的心性世界的錘煉而論,它成為政治領袖、時代的先知先覺者自我規訓、自我挺立、自我決斷的精神指引,賀麟一度稱蔣介石為“王學之發為事功的偉大代表”,其責己之嚴、治事之勤、革命之精誠、事業之偉大,皆由於精誠致良知之學問得來。(27)在有志之士中,用陽明心學乃至宋明理學錘煉自己的人格、培養自己的革命意志已蔚然成風。在《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中,修身的目標被設定為成為“革命家”、成為“革命的聖人”,這就需要“立志”(“真正有決心”)、“自覺”(“真正自覺地始終站在無產階級先鋒戰士的崗位”),並要在“事上磨練”(“共產黨的修養要跟群眾的革命實踐結合在一起”,要經歷“一個很長的革命的鍛煉和修養的過程”)等等,儒家原有修己安人(內聖外王)的框架變成了改造自我與改造社會雙向改造的框架。不過,修身在傳統中是君子的自我要求,而在現代政治運動之中則被泛化為一種道德與政治泯然無別的總體性要求。第二,就培育團體意識而論,它成為現代政黨政治統一認識、提升黨的政策一竿子插到底的貫徹力、執行力的重要思想資源,成為“實行革命主義最重要的心法”。“全民總動員的國家”與政黨政治最終必須訴諸全民性的意志、覺悟與行動力,用孫中山的話說,“革命必先革心”。從梁啟超、孫中山、蔣介石到毛澤東這些現代政治風雲人物紛紛關注知行問題,不亦宜乎!不用說,“全民”之民已經抖落乾淨傳統的“身家”關係。它不再是多元的、具有不同身份的“複合群體”,而是清一色的、擁有統一意志的“單純的同質性”的整體。(28)塑造這種具有統一意志的“群體”便成了中國現代性“教化”的最重要任務,從梁啟超的新民說到劉少奇的共產黨員修養論,這是一“一以貫之”的主題。
最終“國家”與“革命”成為中國知識人心中一個最神聖的觀念。早在《新民說》中,梁啟超就提出在新倫理(家族倫理、社會倫理、國家倫理)構成中,父母對子有生、育、保、教之恩,故子對父母有報恩之義務,而社會、國家之於“國民”其恩與父母同,故國民如不愛國,則“實與不孝同種”。不過,梁啟超明確將“國”與“朝廷”做了區別:國如村市,朝廷為村市之會館,故愛國與愛朝廷並不是一回事:“朝廷由正式而成立者,則朝廷為國家之代表,愛朝廷即所以愛國家也;朝廷不以正式成立者,則朝廷為國家之蟊賊,正朝廷乃所以愛國家也。”何謂“正式”?何謂“不正式”?梁啟超未言,毛澤東在1910年下半年讀到此處加以發明說:“正式而成立者,立憲之國家也。憲法為人民所制定,君主為人民所推戴。不以正式而成立者,專制之國家也,法令由君主所制定,君主非人民所心悅誠服者。前者,為現今之英日諸國;後者,為中國數千年來盜竊之國之列朝也。”(29)1905年,梁啟超在《德育鑒》中明確將“致良知”與“愛國”畫等號,反復強調愛父母、妻子的良知就是“愛國之良知”,在愛國成為“吾輩今日之最急者”時代,人人須以刻刻不欺良知的心法來檢查、省察自己的“愛國心”之誠偽。而在1932年,蔣介石在其《自述研究革命哲學經過的階段》一文中直接呼籲:“愛國家,為國家犧牲,就是個人良心上認為應該做的事情,這就是良知”,否則“只顧逞意志,爭權利,就是在強敵壓境的時候,還要破壞統一,破壞團結,並且借這個機會來反對黨,推倒政府,這就是不能致良知”(30)。到了1943年,馮友蘭就新舊道德加以辨析說:舊道德中的“忠孝”是以家為本位,為父母盡孝、為君主盡忠,但往往會忠孝不能兩全,不能兩全時就要“移孝作忠”;新道德則不同,“現在為國家盡忠為民族盡孝,那就沒有衝突……我們為國盡忠,就是為民族盡孝,為民族盡孝,也就是為國家盡忠”。(31)由於“國家”與“革命”成了終極視界,而對“國家”與“革命”的理解呈現出黨派性與階級性根本性差異,於是傳統修身之中的一些自明的概念諸如天理、良知都成了問題。在“革命”話語中,“既是劊子手又是牧師”的陽明,其“良知”不過是反動統治階級的聲音而已。(32)實際上早在“排滿”與“民族主義”高漲的晚清,章太炎就對“途說之士羨王守仁”現象表示不解,陽明學問“至淺薄”“無足羨”,而且還犯有雙重的政治立場錯誤:“抑守仁所師者,陸子靜也。子靜翦爪善射,欲一當女真,與之搏。今守仁所與搏者,何人也?……以武宗之童昏無藝,宸濠比之,為有長民之德。晉文而在,必不輔武宗蹶宸濠明矣。”陽明所搏擊的對象不是北方的“異族”,故民族大義上是非不明,更為重要的是,他站在武宗立場而不是追隨“有長民之德”的宸濠,故革命是非不清。雙重是非不明,起陽明於地下,會有何辯解?
四 另一個過渡時代的到來:修身會終結嗎?
21世紀是一個“加速”的世紀。科技、社會、生活步調變動速率出現了日益加速的現象。(33)納米技術、生物技術、資訊技術(大數據、物聯網)和認知科學(人工智慧)彙聚為NBIC(Nano-Bio-Info-Cogno)四位一體的“人類增強技術”(Human Body Enhancement Technology),從“外”到“內”、從“身”到“心”(“腦”),對人之“生理”“認知”“道德”各個層面提供了一套增強技術,使得人之聽力、視力、運動能力、耐力、抗疾病與延緩衰老能力、感知、接受、記憶和運用資訊的認知能力以及道德能力(道德判斷、道德情感與道德行動)向著更高、更強、更完善的方向提升。(34)人類增強技術日益成為21世紀的“新道教”,它將道教的“外丹”與“內丹”修煉術完全技術化、程式化、可操作化而且有效化了。人類運用技術從改造自然、改造社會終於“進化”到改造人自身。人類在以工程的方式(engineering way of life)安頓周遭世界的同時,其自身的生命亦日益得到工程化的處理(engineered way of life)。(35)設計與規劃不再只是我們建築活動的術語,也不僅是我們各種工業產品生產製作流程的術語,也是我們政治、經濟、人生乃至生活方式的術語,我們所處的世界日益為工程師所設計、建造、運營、維護與創新,我們的人生本身也成了規劃、設計的對象,最終我們的生命、我們的肉身也不再是“天生的”,而是由我們自己塑造、規劃、設計、加工的。
人類正邁向一個“支配對敬畏的絕對勝利”的時代。人類自由地創造自身,“我命由我不由天”看來正在變成一件“技術活”“體力活”。政治性的“洗腦”與道德性的“洗心”看來都可以通過NBIC流水作業線一勞永逸地加以解決了。這究竟是對自由、尊嚴的一種“增進”抑或是一種“剝奪”,技術進步派與技術保守派各執一詞。上帝無法造出一個只會行善而不會作惡的“人”,因為那意味著人之自由的喪失。這是傳統基督教神義論對“惡”現象的經典辯護。今天如果通過人類增強技術干預人的道德決定,使得原本會做出惡的決定的意識,變成了只能做出善的決定的意識,這是不是值得追求的一件事情?這種工程化的在世方式、這種工程化的人生是不是一種美好的在世方式、美好的人生?人類無比渴望通過增強來使自己變得更健康、更幸福;但另一方面,人類又恐懼增強會產生某些不可逆的人性改變,在先秦,由“人禽之辨”喚起的做人意識,是儒家修身傳統的邏輯起點,在當今“人機之辨”這個人禽之辨的2.0版本所喚起的意識,不再只是簡單的做人問題,因為與“禽獸”這個人的“降格”不同,這個“機”是“人”的升格。升格後的人最終會導致“人將不人”甚或是“人將不存”的困惑。(36)新世紀的人生工程將我們帶進了做“人”還是做“後人類”(Posthuman)這一最根本的生存問題中,“使人類更人性化”,還是“不斷超越人類自身”?這是儒家必須回應的問題。
五 結論
無論在“德性—德行的培育”抑或在“心靈的操練”時代,儘管在修身的目標與具體的技術方面都存在著差異,但二者都分享著一個共同的人性論框架,即天人合一的天道—人道一貫的世界圖景。盡心、知性、知天,人希賢、賢希聖、聖希天,“天”(天道、天理、天德)是修身的終極視野。修身工夫究其實是要成就、培育天性、天心、天情,讓人享受天倫(孝弟慈)之樂。張灝在描述軸心突破中提出一個原人意識的“三段結構”(現實生命的缺憾→生命發展與轉化道路→生命的理想與完成),這個結構跟麥金太爾所說的“三重圖式”(a threefold scheme)即由“偶然所是的人性”→實踐理性與經驗的教誨→“實現其目的而可能所是的人性”是一致的。在古典儒家中,生命的理想乃是鑲嵌在“天—地—人—萬物”這一存在的連續之中,基於“人的覺醒”而產生的“自我—轉化”最終是在這一天道秩序之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另外,由德性—德行的培育向心靈的操練的轉折,雖以“範式轉移”(paradigm shift)擬之亦不為過,但這絕不意味著“修身”傳統的斷裂,毋寧說原來的修身技術仍然有效,理學家依然注重禮儀與行為舉止,乃至遭到世人“幅巾大袖,高視闊步”之譏諷,理學家亦依然重視德性與君子人格的培育,乃至有尊德性與道問學之辯;而就先秦儒學而論,固然德性—德行的培育是修身的焦點,但這也絕不意味著孔子、孟子、荀子等大儒不關注心靈生活,孔子之“操存舍忘”、孟子之“盡心”、荀子之“以心治性”、儒簡《五行》德“形於內”謂之德之行乃至《禮記·大學》正心誠意無不說明先秦儒家從未離“心”而論德。孔子雖從不曾以“聖”自期與自許,但孟、荀均認定人皆可為堯舜、塗之人可以為禹,故宋明理學“聖可學”“滿街聖人”的理念實亦肇始於先秦儒學修身傳統之中。不過聖人皆有異表、萬傑曰聖說,自漢即已成文。唐宋轉型與人皆有佛性、皆可成佛的觀念的流行無疑促成了理學家以“成聖”作為工夫修煉的目標這一共識的達成,而在聖人的心性圖像中更是充分吸納了佛道二教的虛無空靈之精神。要之,旨在“成聖”的心靈操練的理學工夫與德性—德行培育的先秦修身傳統相比,既呈現出連續性,更呈現出更新、突破乃至轉折的面向。或者更準確地說,先秦修身傳統的目標與修身技術成為宋明理學工夫論說的底色,在此底色上,理學家應時代精神而起,出於民族文化慧命的自覺與強烈的道統意識,由各自深刻的工夫修煉體驗出發,濃墨重彩為之增添新的色層,繪製新的篇章。
近代以降,傳統的“天道”被物競天擇的“自然規律”、“社會規律”的“新天道”所取代,修身首先意味著“覺悟”,即從傳統的舊天道(日用倫常的人間秩序)中擺脫出來,從“存有的大鏈條”中擺脫出來,這是一個“解放”的過程,一個現代主體自由、自主覺醒的過程,一個“脫人倫”、離家、出家的過程,人生的意義是在征服自然、改造社會之中完成的,“意義”是“創造”出來的而不是“找”出來的。現代人生在根本上是籌畫、設計、規劃的人生,帶有強烈的“人工性”,而不是“自然性”。
社會烏托邦工程最終演進為人自身的烏托邦工程,即通過一種技術手段可以全方位地改造(提升)人之身心的工程。將人向著更高、更強、更完善的方向提升,只是這個“更高”“更強”“更完善”已經完全超出了“自然”,“人”從“脫人倫”向“脫人身”演進,這裏已經沒有了一個“天性”註定的“自然限界”,因而也沒有“康復”“複其初”的理想模式,人性是無限定的。人的未來、人的命運第一次真正掌握在人自己的手中,在這樣一個時代中,何謂美好生活、美好心性再度成為一個時代問題。原來人類對完美的追求一直以“天”作為“原型”,“天心”“天性”“天德”“天道”“天情”“天樂”一直是儒道兩家共同追求的心性、性情、德性,生命一直作為“禮物”、作為自然之所予(the givens)被感激、被接受、被珍惜,現在這一切都有讓“人”向著“更完美”的方向突破的可能,“天心”與“機心”對決的時代已經悄然蒞臨了。(37)阿多(Pierre Hadot)哀歎說:“我們的確必須承認,人類非但遠遠未能駕馭這種形勢,反而發現正面臨著更嚴重的危險。技術正在導致一種使人類自身日益機械化的生活方式和思維方式。然而,這種文明的無情進步是不能阻止的。在此過程中,人不僅可能失去其身體,而且可能失去其靈魂。”(38)對儒家而言,當人生可以活到一百五十歲,當人造子宮已經成為可以定制的產品,當“人生”不再只是“天生”的,而是“天人共生”,或者說是“天生人造”的,當“我”不再是“個人生活史的唯一作者”,長幼有序、夫婦有別一類的人間倫理與希聖、希天的人生目標,這些儒家修身之道究竟如何開展?《孟子·盡心》以“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的人當追求的論證邏輯看來必須要重新調整,因為傳統修身工夫所著力的“變化氣質”在原則上可以通過一種“增強技術”而“唾手可得”,“修身”不再是一個人的自由問題,而是一個生物技術問題,修身是不是最終會進入一個“終結的時代”?
“加速化”與“全球化”嵌套、牽合構成了21世紀非同以往的特徵。人類與過往的“生存家園”(時間、空間、物、自我、社會)日益“疏離”與“異化”,而因“全球化”催生的各種各樣的民族與宗教的激進主義更讓全球出現了動盪不安的態勢。查爾斯·泰勒所謂的“現代性的隱憂”又出現了新的形態。“加速”的世界就像一匹脫韁的野馬,從不會停下步伐等待駕馭它的主人。哲學與道德的反思必須跟上這個世界的節奏才能發揮它應有的作用。它必須對21世紀新出現的問題給出自己的解決思路。儒家修身傳統在數千年的演化過程中,表現出“常”與“變”的張力,它在應“變”中既保守其“常”,又賦予“常”以新的意義;它在守“常”中既應對其“變”,又規整、調適著“變”的方向。如何在“加速化”與“全球化”的時代中,在跟上這個加速化的時代節奏“隨波逐浪”的同時,儒學必須“截斷眾流”,對此類問題給出有效的回應,也惟有如此,儒學修身話語才能在當今“中國話語”的建設中發揮其中流砥柱的作用。
注釋:
①陳來:《古代思想文化的世界:春秋時代的宗教、倫理與社會思想》,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2年,第16頁。
②李巍:《從語義分析到道理重構——早期中國哲學的新刻畫》,北京:商務印書館,2019年,第108-109頁。
③餘英時:《論天人之際:中國古代思想起源試探》,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4年,第236、246-247頁。
④閻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第50頁。
⑤餘英時:《中國知識人之史的考察》,《現代危機與思想人物》,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5年,第3頁。
⑥餘英時:《士與中國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02、107、120-126頁。
⑦楊儒賓:《儒家身體觀》,臺北:“中研院”文哲研究所,2003年修訂二版。黃俊傑:《“身體隱喻”與古代儒家的修養工夫》,《東亞儒學史的新視野》,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年。
⑧Philip J.Ivanhoe,Confucian Moral Self Cultivation,Peter Lang Inc.,International Academic Publishers,1993.對孟、荀修身路徑之最新闡述可參彭國翔《“養氣”與“盡心”:孟子身心修煉的功夫論》(《學術月刊》2018年第4期)、《“治氣”與“養心”:荀子身心修煉的功夫論》(《學術月刊》2019年第9期)兩文。
⑨功夫、工夫一詞語義之演變參林永勝:《功夫試探——以初期佛教譯經為線索》(《臺大佛學研究》2011年第21期)、《反工夫的工夫論——以禪宗與陽明學為中心》(《臺大佛學研究》2012年第24期)兩文。
⑩楊儒賓:《〈中庸〉、〈大學〉變成經典的歷程:從性命之書的觀點立論》,收入李明輝編:《中國經典詮釋傳統(二)儒學篇》,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4年,第113-158頁。
(11)劉蕺山雲:“《大學》一書,程朱說‘誠正’,陽明說‘致知’,心齋說‘格物’,盱江說‘明明德’,劍江說‘修身’,至此其無餘蘊乎!”見黃宗羲:《師說》,沈芝盈點校,《明儒學案》,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13頁。
(12)陸九淵:《陸象山全集》卷三十五,北京:中國書店,1992年,第303頁。
(13)馬永卿輯、王崇慶解、劉安世著:《元城語錄解》卷上,北京:商務印書館,1939年,第8頁。
(14)王塘南撰:《友慶堂合稿》卷六,錢明、程海霞編校:《王時槐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589頁。
(15)陽明江右門人羅念庵(1504-1564)即預先自覺其死期,死時“正巾斂手,端默如平日。”(事見胡直所撰行狀,徐儒宗編校整理:《羅洪先集》“附錄一”,南京:鳳凰出版社,2007年,第1386-1387頁)羅近溪(1515-1588)曾有一名言“真正仲尼,臨終不免歎口氣”,但他本人自幼即立志“尋個不歎氣的事做”。及其臨終(九月初一日),羅子自梳洗,端坐堂中。命諸孫次第進酒,各各微飲,仍稱謝隨。拱手別諸生曰:“我行矣,珍重珍重!”諸生懇留。羅子愉色許曰:“我再盤桓一日。”乃複入室,初二日午時,羅子命諸孫曰:“扶我出堂。”整冠更衣,坐而逝。(事見方祖猷等編校整理:《羅汝芳集》,鳳凰出版社,2007年,第851頁)王心齋(1483-1541)之子王東厓(1511-1587)臨終,命弟子輩雅歌取樂,旁有人見其氣定,令扶起更衣,東厓曰:“是速之也,須令其從容俟氣盡行之。”少頃,瞑目斂容以逝。(事見《明儒王東厓先生遺集》,收入王艮撰、陳祝生點校:《王心齋全集》,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211頁)杜見山(1521-1601)年八十餘,小疾。語友曰:“明晨當來作別。”及期,焚香端坐曰:“諸君看我如是而來,如是而去,可用得意見安排否?”門人請益,良久曰:“極深研幾。”遂瞑(事見王崇炳撰:《杜見山先生傳》,《學耨堂文集》卷四)。對中晚明心學一系生死關切議題之考察見彭國翔:《良知學的開展:王龍溪與中晚明的陽明學》,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5年,第463-480頁。
(16)理學文獻中著名的《定性書》即是程明道與張橫渠切磋工夫的書信。陽明再傳弟子胡廬山(1517-1585)每日將自己全天的活動加以檢點,且記錄在案以自箴而自驗,去世後門人檢其遺文,得一密笥,“啟之,冊不盈尺,皆手書,名曰《日錄》。每歲一帙,日有書,時有紀,自卯至寢,自幾微念慮以至應對交接,工夫純疵,毛髮必書,即夢寐中有一念盭道者亦書”。(郭子章:《先師胡廬山先生行狀》,張昭煒編校:《胡直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998頁)關於儒家自我書寫修煉傳統請參Pei-Yi Wu,The Confucian's Progress:Autobiographical Writings in Traditional China(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0)一書。
(17)在儒家中,這一模式當然可上溯至李翱的《複性書》。阮元在《塔性說》《複性辨》兩文中指出,佛教“有物焉,具於人未生之初,虛靈圓淨,光明寂照,人受之以生,或為嗜欲所昏,則必靜身養心,而後複見其為父母未生時本來面目”,此“物”究何名耶?無得而稱也。“晉宋姚秦人翻譯者執此物求之於中國經典內”,發現《莊子》中“性”字本是天生自然之物,“《駢拇》《馬蹄》之喻最為明顯,莊子曰:‘繕性於俗,學以求複其初,謂之蒙蔽之民。附之以文,益之以博,文滅質,博溺心,然後民始惑亂,無以反其性情而複其初。’是莊子此言複性謂複其自然也。晉人讀考莊者,最重自然,故與佛所謂性相近也,李習之《複性書》之複初,則竊取佛老之說,以亂儒經,顯然可見也。”阮元撰、鄧經元點校:《揅經室集》,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1059-1060、1061頁。其實《淮南子·淑真訓》已將儒家的聖人之學與複其初聯繫在一起了:“是故聖人之學也,欲以返性於初。”高誘注:“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孟子曰:性無不善,而情欲害之,故聖人能反其性於初也。”
(18)[美]列文森:《儒教中國及其現代命運》,鄭大華、任菁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第87頁。
(19)羅志田:《近代中國“道”的轉化》,《近代史研究》2014年第6期。
(20)[法]孟德斯鳩:《孟德斯鳩法義》,嚴複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1年,第373頁。
(21)[德]施密特:《政治的概念》,沈雁冰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30頁。
(22)王汎森指出劉師培《倫理教科書》已經意識到要讓人民有公德,就要成立“完全社會”、推行“社會倫理”,而要成立完全社會就要有“黨”。見《從“新民”到“新人”》,王汎森著:《思想史生活的一種方式:中國近代思想史的再思考》,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年,第39頁。
(23)章太炎:《社會通詮商兌》,《章太炎全集·太炎文錄初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349頁。
(24)張灝指出,家庭倫理在梁啟超那裏尚未成為國民發展的障礙,這可能與他受到日本忠孝一體的觀念影響不無關係。張灝:《梁啟超與中國思想的過渡(1890-1907)》,崔志海、葛夫平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91頁。
(25)馬鏡泉等點校:《馬一浮集》,第3冊,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1053頁。
(26)[英]麥金太爾:《追尋美德》,宋繼傑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11年,第40頁。
(27)蔣介石與陽明學之關係,見黃克武:《蔣介石與陽明學:以清末調適傳統為背景之分析》,黃自進主編:《蔣中正與近代中日關係》,臺北:臺北稻香出版社,2006年,第1-26頁。
(28)張灝:《五四與中共革命:中國現代思想史上的激化》,《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輯刊》第77期。
(29)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澤東早期文稿》編輯組編:《毛澤東早期文稿(一九一二年六月—一九二○年十一月)》,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頁。
(30)劉健清編:《中國法西斯主義資料選編》(一),北京:中國人民大學中共黨史系,1985年印行,第109-110、117頁。
(31)馮友蘭:《當前的幾個思想問題之一:新舊道德問題》,《三松堂全集·中國哲學史補二集》,北京:中華書局,2017年,第411頁。
(32)楊天石:《王陽明》,北京:中華書局,1972年。值得注意的是,蔣介石三十年代在江西圍剿紅軍時期,就親自編訂了《王陽明平贛錄》一書,期望對“今共匪蟠擾之地”(“昔陽明平賊之地”)所開展的清剿前途有所補益(見蔣委員長編:《王陽明平贛錄》,上海:青年與戰爭社,1933年,“序言”,第4頁)。王任叔以“剡川野客”為筆名於1941《大陸》第1卷第6期發表《王陽明論》一文,徑斥王陽明“把‘國家至上’‘民族至上’統統歸納到皇帝老子底‘心術至上’裏面去”,並明確指出,王陽明治理南贛汀漳所推行的十家牌法,在“剿匪時代”,武漢南昌一帶也著實奉行過。無疑,王任叔在這裏深刻揭示了現代政治之中“國家”、“民族”與“心術”捆綁在一起的情形。
(33)[德]羅薩:《新異化的誕生:社會加速批判理論大綱》,鄭作或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
(34)相關文獻見[意]羅西·布拉伊多蒂:《後人類》,宋根成譯,鄭州:河南大學出版社,2018年;[法]呂克·費希:《超人類革命》,周行譯,長沙: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2017年;[美]凱瑟琳·海勒:《我們何以成為後人類:文學、資訊科學和控制論中的虛擬身體》,劉宇清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年;[美]弗朗西斯·福山:《我們的後人類未來:生物技術革命的後果》,黃立志譯,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7年。
(35)[美]米切姆:《一種工程的生活是否值得人類去過》,《哲學分析》2019年第2期。
(36)陳少明:《儒家倫理與人性的未來》,《開放時代》2018年第6期。
(37)[美]桑德爾:《反對完美:科技與人性的正義之戰》,黃慧慧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年。
(38)[法]皮埃爾·阿多:《伊西斯的面紗:自然的觀念史隨筆》,張蔔天譯,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9年,第211頁。